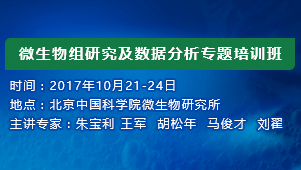王红阳:探寻肝癌基因密码
来源:东方早报 发布者:张荐辕 日期:2015-07-01
为了揭示肝癌的奥秘,王红阳的人生轨迹从此与众不同。从一个消化内科医生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从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的课题组长到第二军医大学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创始人,她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国创业,终于在以肝癌为主的肿瘤机制研究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王红阳
1952年出生于江苏徐州,肿瘤分子生物学与医学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综合治疗二科主任,主任医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是肝癌大国,全世界有一半的肝癌在中国。除了一把手术刀,医生还能为肝癌患者做些什么?如果能揭秘肝癌发生的基因密码,是否能找到攻克肝癌的金钥匙?
为了揭示肝癌的奥秘,王红阳的人生轨迹从此与众不同。从一个消化内科医生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从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的课题组长到第二军医大学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创始人,她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选择了科学道路上的探索和坚守,回国十多年终于解开了肝癌的谜团,在以肝癌为主的肿瘤机制研究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王红阳院士团队最新研究发现了肝炎向肝癌转化过程中新的关键节点分子,有的成为肝病分子分型的标志物,有的作为新的药靶分子进入靶向化合物筛选阶段,自主研发的肝癌诊断试剂盒已经通过审批,即将应用于临床。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在《癌细胞》、《自然通讯》、 《美国胃肠病学》、《肝脏病学》、《消化道疾病》等国际主流期刊,解放军总后勤部为王红阳院士团队荣记集体一等功。
63岁的王红阳仍然充满了对科学探索的激情,她说,“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到临床应用,造福于患者才是最重要的。医学转化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我就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基础研究创新发现,到临床应用转化,现在肝癌诊断试剂盒的发明,真正做到产学研用的结合,我为此感到自豪。”
解密基因信号传导
作为生物遗传载体的基因DNA,是生命最小的单位,也是生物体的调控器,肿瘤的发生也与基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基因也是有语言的,基因的语言就是生物信号。细胞的生长、分裂、衰老、癌变和死亡是一个信号传递的过程,并有许多基因的参与。通过生物信号的研究,可以从异常中发现规律,进而破解肿瘤基因的密码。王红阳就是通过生物信号,识别基因语言,并与之对话的人。
王红阳解释说,“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如果癌基因过度激活,人体就会生长肿瘤,如果抑癌基因正常稳定执行功能,就能控制人体不生肿瘤。肿瘤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遗传基因和宿主免疫状态是肿瘤发生的内因,而外界环境的刺激,如放射线、水源污染、病毒传播等外界因素,使体内的癌基因过度激活,就会生长肿瘤。”
肝癌中有哪些重要的癌基因?如何控制不让其激活?要找到肿瘤的标志物,就能阻断癌症的发生。这些非常基础的研究一旦与临床结合起来,就能从人群中把肿瘤病人诊断出来,并及时进行干预阻断。王红阳就锁定了基因研究,希望找到攻克肝癌的钥匙。癌症研究之路绝非一蹴而就,王红阳一路坚守,不忘从医的初心。
1952年王红阳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1972年,年仅56岁的父亲因肺癌晚期去世,已经参军当护士的王红阳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学医当一名医生。1973年,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她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毕业分配到长征医院当了一名消化内科医生。随着工作实践的增多,她渐渐感到知识不够用了,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发奋学习,1981年考取第二军医大学消化免疫学硕士,毕业后回到原来的岗位工作。
然而,面对消化道肿瘤病人,作为一个消化内科医生的她感到无能为力,每当看到这些病人临终时对生命的留恋,她就不由自主想起父亲和当初立誓学医的誓言。她认识到,攻克肿瘤,解除病人痛苦,仅靠一把手术刀是不够的,必须要找到肿瘤发生的机制,从基础临床研究做起。经过这样的大彻大悟,她开始了解医学领域前沿的最新动态,不知不觉掌握了很多分子生物学、细胞学的新知识。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之人。1989年,第二军医大学有两个留学德国的名额,时任二军大副校长的吴孟超教授慧眼识珠,力荐王红阳。她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获得留学德国的机会,从此与基因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9年到1992年,她在德国乌尔姆大学医学院临床生化专业攻读博士、博士后,1992年到1998年,又在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后,一直做到课题组组长、高级研究人员。整整十年,弹指一挥间。细细回味,甘苦自知。
在德国期间,王红阳痴迷于基因的信号传递研究,从宿舍到实验室,两点一线,每天在实验室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1995年6月11日,经过一年半的反复试验,王红阳终于克隆了一个新基因,并取名为“PNP-1”,然而当她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德国导师Axel Ullrich时,这位马普生化所所长、国际公认的细胞信号学权威,却不无遗憾地说:“日本科学家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发现了,日本科学家已经将它命名为BAS。”
此时王红阳的脑子一片空白,她明白,科学领域只有第一,任何步其后尘的,哪怕只有半步之遥,也不会载入史册。但她不甘心这数百天的心血付诸东流,她告诫自己,一定要挺住,也许会柳暗花明的。一种紧迫感,让她开始了科学实验的第二次长征。
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1997年初,王红阳在国际上首次鉴定出PCP-2这一受体型络氨酸磷酸酶,提出MAM型络氨酸磷酸酶家族新概念,获得国际专利,并在世界人类基因库登录。在短短六年时间里,她和她的课题组在国际上先后首次发现、克隆、鉴定了人类及鼠类重要的6个新基因,并全部在世界基因库登录。她撰写的10多篇研究论文在《自然》、《致癌基因》等国际核心期刊发表,她连续两届当选为德国慕尼黑地区旅德中国学者生命科学协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德医学协会和中华医学会实验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分课题项目负责人。
回国后白手起家
在德国的十年,王红阳一直与母校二军大保持着联系,帮助母校培养研究生。虽然已在德国取得很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但王红阳仍一直心系祖国的肝癌研究。
于是,当恩师吴孟超院士召唤她回国创业时,她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踏上了回国的旅程。1997年初,她从德国带回250万元的科研设备,在东方肝胆医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际合作生物信号传导研究中心,她穿梭于慕尼黑和上海之间,致力于中国生物信号传递研究方面的发展。
按理说,早已功成名就的她完全可以选择一个轻松工作,为何要回国再创业?她说,“我不甘心这样下去,还是想做肝癌研究。当时完全可以到中科院做研究,但是只有东方肝胆是国际最大的肝癌临床中心,地处上海,病人资源丰富。吴孟超院士也认识到,光靠开刀解决不了肝癌问题,必须要做肝癌诊断治疗、发病机制的研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实验室把肝癌研究做起来。我对吴老和二军大,也有一种感激。”
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是艰辛的,尤其是在临床医院从事基础研究。“我刚进来的时候像个异类,很多医生不理解你在干什么,大家没有共同语言。但吴孟超院士支持我的研究,坚持院所合一的发展方向。从招收第一个研究生,到处游说,从一个空房子里建立起实验室,甚至连实验用水也是一瓶瓶从德国带回来的。当时教育部的启动经费3万元,从德国科学院拿到每年10万马克的支持,为了节省费用,我们在医院到处找废瓶子消毒后做实验。经过18年的发展,现在实验室条件已经超过德国的实验室。”
对科学的好奇心是王红阳不断探索的原动力,王红阳说,“全世界50%的肝癌在中国,为什么中国人肝癌发病率这么高?肝癌发病机制到底是什么?科学的好奇心驱动你做创新的事。另一方面,父亲身患恶性肿瘤去世的事情也触动我,中国每分钟就有6个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多少家庭被这个疾病毁掉了?这也是我从事肿瘤研究的动力。”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王红阳创办的第二军医大学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综合治疗病区,已经建成国内首个样品规范、资料齐全的肝癌样本库,形成基础与临床结合的创新研究基地。在分子诊断方面,筛选和研发了新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及血清检测单克隆抗体,获国内外发明专利和临床应用推广;首次发现新的抑制性受体对肝癌细胞生长、凋亡的调控机制和癌基因P28在肝癌的异常信号网络,为肝癌防治提供了新的靶标;分离和鉴定新的酪氨酸磷酸酶3种;发现了受体型磷酸酶PCP-2调控β-catenin介导的肿瘤信号通路,阐明Wnt通路中酪氨酸磷酸酶调控的重要作用与作用机理,对酶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让肝癌诊断更准确
在中国,肝癌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与肝炎高发密不可分,但对慢性肝炎发生和转归的分子机制认识严重不足,缺少有效干预和治疗手段,难以阻断大量病患从慢性肝炎向肝硬化和肝癌发展。
近5年来,王红阳带领研究室深入解析肝脏炎-癌转化的分子网络调控机制,率先提出了肠道稳态失衡在肝脏炎-癌转化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发现了其中关键的分子纽带;进一步明确了以巨噬细胞和星状细胞为主的非实质细胞在肝脏慢性炎症和恶性转化中的主导地位,阐明了以TLR通路异常活化为核心的肝脏慢性炎症调控机制;发现了上皮-间质转化(EMT)在炎癌转化中新的分子决定机制,并实现了有效干预;鉴定了新的肝癌起始(干)细胞亚群,确定了炎症微环境促进肝癌起始(干)细胞自我更新的关键信号通路和转录因子。以上鉴定的炎-癌转化过程中新的关键节点分子,有的成为肝病分子分型的标志物,有的作为新的药靶分子进入靶向化合物筛选阶段。
研究室还提出了通过益生菌等保护肠道,可改善肠道稳态,抑制肝癌发生及靶向关键节点蛋白Gankyrin等,多途径阻断炎症恶变等干预炎-癌转化的新策略,为肝病防治与新药研发奠定了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多本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美国胃肠病学杂志、肝脏病学杂志等多次刊发述评给予高度评价,研究成果获得2014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
“前面这么长时间的研究积累,为认识这个世界和科学奠定了基础,现阶段到了研发新药、诊断试剂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把研发成果转化为临床,找到治病救人的方法和手段。”王红阳说。
在国家科技专项课题等的支持下,王红阳团队应用多种高通量手段鉴定一批肝癌诊疗标志分子,获授权专利16项,多项成果进入试剂盒研发和药物靶标研发阶段。2014年,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基于新肝癌标志物Glypican-3肝癌检测诊断试剂盒通过国家药监局审批,获正式注册应用于临床诊断,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具有完全自主产权的单克隆抗体为基础研发获批的新型试剂盒,对于肝癌的病理诊断与分型,尤其是肝癌疑难病例的良恶性的鉴别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该项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
王红阳解释说,“传统的甲胎蛋白作为肝癌常规诊断检查指标,只有40%~50%的准确性,有一半会漏诊。我们发现的Glypican-3肝癌检测已得到国际公认的标志物,从发现-证明-诊断试剂盒,产学研连成一线。两项合用,使肝癌诊断准确性提高15%~20%,已经获得国际发明专利,将在临床应用推广。”
而靶标基因的筛查可以作为新药研发的化合物,掌握了靶向基因技术,就意味着研制肝癌特效药不再是梦想。
王红阳说,“比如P28基因,就是一个肝癌的靶标,90%的肝癌都是过度激活这个基因,而传统的甲胎蛋白只在40%的人群中有高表达。因此如果能找到这个基因的抑制剂,就可以开发新药。目前我国的高端医疗市场都被进口药物垄断,我们猛然意识到,解救我国的肝癌患者一定要有原创的我国自己的新药。然而,新药的开发过程很漫长,常常需要十几年。我们现在与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合作,期望能加快进程,少走弯路,早出成果。现在国家新药重大专项催生许多创新研究,十年后会看到更多的中国药。”
相关新闻
- 2018/03/27
- 2018/03/27
- 2018/03/16
- 2018/03/16
- 2018/03/09
- 2018/03/05
- 2018/03/01
- 2017/02/06